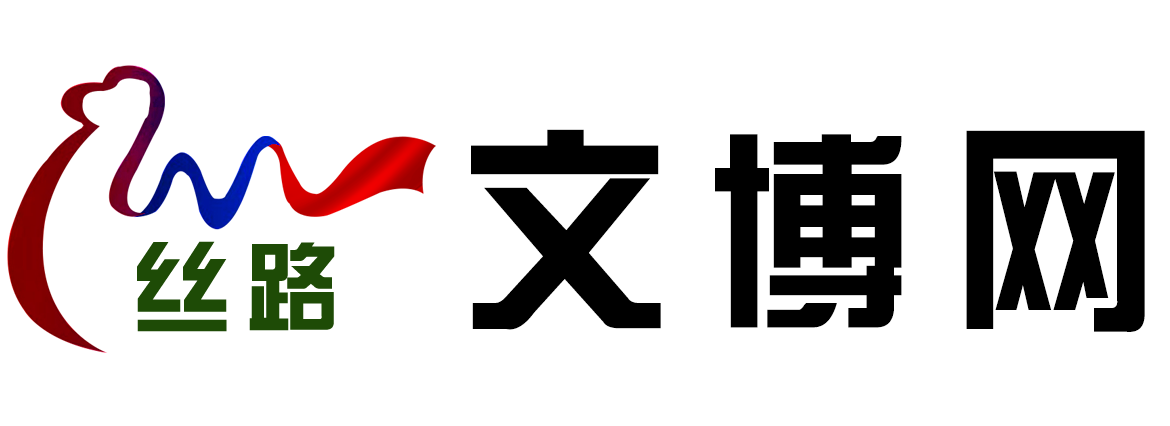甘天枝||父亲的时光
发布时间:2022-01-11 10:26:50分享: 编辑:芳菲
父亲的时光,是一个家族的时光,也是一个时代的时光。因为儿女走过的所有历程,无不打上父亲山一样伟岸厚重的时光烙印。
父亲说,自己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,一生有四件憾事,四件幸事。
四件憾事:一件是他平时爱看点书,爱学新东西,却没机会能走进大学校门。一件是抗美援朝那年,他作为党员先进典型去朝鲜慰问志愿军,可到了鸭绿江畔,说对面战事吃紧,就没能过江见上志愿军。一件是他二十岁那年敦煌县招干部,他被推选为干部苗子,独子的他,因怕农村的老大大(父亲)无人看管而受罪,三亩土地无人种,粮食不够吃,便放弃了去县里当干部的机会。一件是祖宅被大水冲毁后,他没能把它重新盖起来。临离开这个世界了,没能最后回去看看那个他渡过半生的老家,没能最后见一面和他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伴儿。
四件幸事:一件是他十九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当了好多年的村干部。一件是他的家出了几个能人(三个公务员、一个教授,一个工程师)。一件是他家里出了一名军人,在部队当了十几年兵(我)。一件是他儿子出了一本大书(长篇小说《栅栏那边的羊群》上下卷八十多万字)。
父亲在对自己评价时说,他的成绩和缺点各占五十分。我问他,为啥缺点占了五十分,他说:一个人,当机会来了不去想办法抓住,而让它像水一样流走,这个错误每出一次,都是翻倍加倒分的。
父亲是这样约束自己的,也是这样教育他的孩子们。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,村里有一个干部对父亲说:学校里放寒假了,你的娃娃不让去村里干农活,圈在家里干啥呢?父亲说,我不想让娃娃再刨土疙瘩,我要让他们在书本里去找黄金屋。不知道他是否听懂,但他却用极其奇怪和复杂的眼神看着父亲,半会才说:你总没有白日做梦吧?父亲说,梦还得个人做。
到八十年代以后,父亲的人生梦就陆续实现了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,从部队转业前夕,我想,当兵十多年,也没尽上孝道,便将父亲从敦煌接到甘南草原,在部队驻地为他租了一处房子,想让他在这里享享儿子带给他的一份清福。
由于我的转业安置手续被发回了家乡,和父亲商量时父亲说不行一起回老家吧。最后我还是确定,留在为之贡献了全部青春的甘南高原。
我决定尽快回乡去办回工作手续。
当我半月后将手续从老家办回甘南,走出汽车站,忽然看到了父亲的身影。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提着包,赶忙寻声找了过去。
果然真的是父亲,他在一个小卖铺前,正用一杆小秤收废纸板子。刹那间,自尊烫伤了我的虚荣心,三步并作两步我走过去,一把夺过父亲手中的破纸盒和秤,撂在了一边,拉起父亲就要离开。
父亲急了,一边挣扎,一边往后看,企图用他最朴质的感受表现他微妙的情感:我收来的旧纸盒还在那里,那是掏了钱的,他们不会替我保管的。
我平生第一次给父亲发脾气:大大,谁让你到这里收废纸盒的,看看你满身的灰尘泥土,你不知道丢人现眼的吗?
父亲这时才突然感到愧疚得有些疼痛,忙解释:娃子(孩子)啊,我不是有意让你难堪,丢你的人。你走时留的钱我怕不够用,现在市场经济嘛,我想来个鸡生蛋,蛋孵鸡,滚动一点钱,这样,就可以减轻你的负担,你刚从部队转业下来,还没工资……
我说,我没负担。不过,就是有负担,我也不能告诉父亲。
我们向前走了一段路,父亲见周围人迹稀少了一些,便又小声和我商量:娃子,先把这一次的纸盒买了,以后就不做了。
我说,不是我生气,大大啊,您受了一辈子苦,也该享享福了。这次,我接您来,就是想让您从此不再受苦,安享后半生的幸福时光。不是让您刚出辣子地,又进茄子地。
父亲用袖子擦了擦满头的汗水,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,低下眉眼,然后又说:娃啊,山不争高,水不争流。我这一辈子都栽在泥土里,从来不怕脏和累,能吃苦是咱农民看家的本钱,如果我不要在咱租房附近收废纸盒,走远一点你看行不行?
说了半天,他还想去收废纸盒,我很果断地说,咱回家!
父亲看了一眼身后的那一大堆纸盒子,有些恋恋不舍的跟我回家了。
一路上,父亲一再絮叨,那堆纸盒,我掏十四块钱买的,算了算最起码也能赚回八元钱!
后来,他又背着我帮着半山人家去种青稞、油籽,我也只好默认了,因为,那毕竟是父亲自己的时光啊。
七十岁那年,父亲回了一趟敦煌老家,就像他说的,他有一种荣归故里的感觉。那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回老家。回去的原因是因为老宅子被水冲垮了,他要安排这些善后事宜,顺便去上坟。
说来也巧,那个曾经讽刺过父亲的村干部,正在地埂上坐着晒太阳,忽见父亲走在对面的小路上,他拄着拐棍站起,蹒蹒跚跚迎了上去,颤悠悠的拉住父亲的手,用干涩的眼神望了他半晌,才说:老家伙,你比我要大十来岁的呀,我前年就得靠拐棍走路了,可你还像个老小伙子,走起路来风都能把人煽翻。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他,而是用手遮阳向宽阔无垠的农田望了一圈:娃娃们呢?老村干向西一指:都在那片地里种庄稼哩。
父亲点了点头没说什么!
看到老村干不到七十岁就衰老成了那样,他心里多少有些内疚。当年,自己犯了一个大错。他为啥只顾自己的娃娃,就没去劝劝他,让他也把娃们圈在家里去啃书本子,不要逼娃娃去田里干农活,将来准能考上大学,跳出农门,当上干部。今天,他一定也不是坐在这个土坎子上发呆,一定也能像自己一样,浑身一尘不染,坐在娃们创造的黄金屋里,逍遥自在,吃穿不愁。
这一天是清明节,父亲本来要先去上坟的。但他还是放下了一切事情,和老村干坐在田垄上,唠起了许多年都没有一起唠过的嗑。
父亲抓起一撮土,说:其实,还是坐在土地上踏实啊。
老村干一见父亲和过去一样没架子,还在乎他,看得起他,他脸上挂满了自豪的颜色。遂叹了一口气,说:一辈子就像喝了一杯水,没隔着,就喝干了。当年一起爬冰卧雪,进山挖烧柴、修水渠修水库、拉土粪整农田的老农们,现在一个个都见了阎王爷。王勃比你大一岁,去年就没的。史兴华比你小三岁,他的娃子当了几年村主任,前年落选了,就跟着娃们去新疆一个单位守大门,今年春节也没了。老苟和你同岁,他在肃州跟着娃子享了一年福,也走了。你前后的老爷子老婆子都没了,我前后的人也走得没剩下几个了。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了,有到沙州古城开旅社的,鸣沙山月牙泉开铺子的,莫高窟搞旅游的,市里开出租车的。年轻人一走,村里的土地大多都没人种了,荒芜了。村里,你在时有一百多户人,现在,只剩下几十户了。现在的村长是越当越小了,人和事情却越来越难干了。大一点的家户有张家的、梁家的、岳家的、赵家的等等,再就是从外地迁移来的几户,能种地的,都是没读完中学又不愿出去打工的。你看看,全村见不到一头牛,找不到几只羊,听不到鸡打鸣猪嚷嚷。倒是狗多了几倍,它们替主人守着村子里的破大门。哦,我还差点忘了告诉你,老队长何癞瓜子,你的老搭档,他如今也进城了,他比你大十一岁哩,他娃子在城里上班,买了房子,给他在二楼的平台上搭了一间简易房,一日三餐,一顿不落,老汉过得很好。去年冬天我见他时,脸吃得红扑扑的,和你差不多,满福得很。不过,你住的是楼上的主卧室,何癞瓜子住的简易房还生炉子,他和你差远了,差远了。
没料到,老村干第二年也离世了,何癞瓜子却还活着。
父亲知道后,默默地摸了好久泪水。他也因此像变了个人似地,一段时间话都不多说了。
有一天,吃过晚饭,父亲叫我到他的卧室坐坐。
父亲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皎洁的月色,说:又中秋了。娃啊,人越老,对家乡的恋念好像越重。其实自从你们姊妹考学的考学,入伍的入伍,工作的工作,你妈妈给你的弟兄看娃娃走了以后,咱的家,早已是一座空庙了,可我内心那种牵挂,却是丝毫没有减弱。梦里总是在咱老家四合院前后的果园子里转悠。房屋四周那上万棵的白杨和柳树,哗哗作响的树叶那么熟悉亲近,那可都是我在家时栽下的啊。还有地里的韭菜、小葱秧、蒜苗子,是那么绿那么壮实。那个杏子啊,还是那么金黄金黄的,老远就能闻到它的香味。这一段,我总想回敦煌去看看。老家和我年龄前前后后的人都没了,现在虽然离开那里了,毕竟我还活着,过去,和他们一起也为改变村子的面貌争争吵吵了半辈子,人走了,情还是留在那里的啊。我回去也不为别的事,就想在家乡那片沙土地上,给他们奠个纸,絮叨几句。
我说:您多年都没回去了,现在的人们或许早己记不起你了……
父亲眼里噙满了泪花:娃啊,他们记起记不起我,倒是小事了,可我记着他们,没忘了那片土地啊。有些事,有些情你们不懂啊,你不懂我们那一代人的心里究竟在想啥,究竟期盼啥啊。
我不知该说什么。
父亲用袖口沾沾眼角:干柴火,拉风匣,大锅饭,是老家的味道。狗叫鸡鸣,猪走牛吼,是乡下的声音,那是另一种情感,是忘不掉的乡情啊。
如今父亲的心情应该比以往好多了,可父亲的另一种情感里包含的深切含义究竟是什么?,有时侯,我真的也不完全弄不懂。
我答应,等我工作闲暇一些了,一定陪他回去一趟。
可是,工作似乎就没有闲过,每天都是匆匆忙忙,忙什么,自己也不明白,这也使得父亲最终没能再回一趟老家去。
父亲见我一直很忙,也变了口气:娃子,问问你妈妈,如果方便,就回来吧。
这个时候,母亲身体也不好,对母亲身体不好的事,我怕父亲揪心,也没告诉他。
这天周末,有个叫九哥的朋友叫我去吃饭,席间,他忽然靠近我,有些神秘兮兮地说:你这人,看是人也好着哩,又有才情,我就想不通,你咋就对自己的老人不好呢!不管做多大事,孝敬父母才是最大的事啊!
听了这句话,我好莫名其妙,但心情瞬间就恢复了平静。
我问九哥,这话,你是从何说起的呀?
九哥摇摇头:我不喜欢和不孝敬父母的人打交道。
从此,九哥再也没和我联系过。当然,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话,我也没在乎它什么,仍然做着自己该做的事。
八小时以外,我不间断地下功夫写书,我给父亲承诺过,要在他的有生之年,完成那部八十万字的大书出版,让他亲自读一遍。
那年,父亲动了前列腺炎手术,这样,他在高原的生活也越来越不适应了,经常是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,总感觉冬寒夏冷,心脏、呼吸都成问题。
我就将部队转业费的全部,又借贷了一些款子,在一个气候适宜的小县城买了一套房子,将父亲安顿到了那里。
父亲到了新的地方后,比在甘南居住时的身体好多了。一年后,他的健康状况明显恢复,一切如常。我的心里,也舒畅了许多。
可眼见父亲一天天老了,我写书的进展因为琐事影响似乎越来越慢。
因为,只能在工作之余,只能谢绝一切朋友的相约,埋下头加班加点去写。
为了完成自己既定的目标,为了完成我承诺父亲的愿望。十多年啊,不知遇到了多少的艰辛坎坷,还有各种不完美的人和事,让我失掉了许多不该失掉的东西,这成了我一生难于挽回的憾事。当然,有人说,上帝为你关一扇窗户,就会为你打开一扇门。当我的长篇小说《栅栏那边的羊群》出版,来自远方的一部汽车,将属于我的那些书籍送到我家门口时,那一夜,抱着书,我哭了许久许久。我不知道,我该怎样表述那时的心境,那个哭,完全可以算是对所有失去岁月的一种祭奠吧。
周末,我回到父亲居住的那个小城市,当我亲手把书捧给父亲时,父亲高兴得几天都没了瞌睡,通宵达旦的阅读了起来。他说:过去一直读别人的书,终于读到了儿子写的书。
父亲一口气读了四遍后,每次,一见我回家看望他,总要和我谈论小说中的那些人物,如才华加、老村长、瑶草、老阿妈、老支书、罗布藏、卡布,尤尕四那些牧人,书中所有人物的名字他几乎滚瓜烂熟,故事情节能了如指掌。父亲说:你描写的那些个人啊,真是活灵活现,人物的脾气性格让我难以忘记,他们就像一直站在我的眼前,久久不愿离去……
其实,说起父亲识字的过程也是挺辛酸的。他小时候,总在私塾先生的门外,偷偷听有钱人家孩子的读书声,教室里面的孩子没背会的课文,父亲竟凭借先生反复的朗读,背会了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《百家姓》。后来见父亲苦爱读书,私塾先生破天荒不收钱让他进门读书……
父亲说,你从十八岁入伍一去甘南牧区就是三十多年,对草原的情感至深,能从书中读到。对草原牧民的了解,胜似你家乡和亲人。这一点,可贵啊。读了你的书,也能看出党在牧区脱贫所倾注的大量心血,值得讴歌,值得每个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感恩戴德,永不忘记。
我说,我还在写一本书,对于过去的事,走过的路,我会在即将出版的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《走失的牧场》里详细记述。那是一部自传体小说,也是我对人生和社会的另一个缩影,里面有周围许多熟悉的人和事。正义的、忠实的、狡猾的、投机的、双面的等等,在现实中都有原型。其实,有些人在我心中本来很高尚,有一天,他忽然在我面前倒塌了,我真为这些人可惜,他也失去了一生最美丽的机会。
这一夜,我和父亲聊了很久。
只可惜,那部书,父亲读不到了。
第二天早上,远方传来消息,说母亲的病情加重了,还说,她很想见到父亲。因为母亲曾有话,如果她病了,就赶快把她送到父亲身边去。我告诉她身边的亲人:尽快想办法把母亲送过来。
正在这个节骨眼上,父亲却在户外无意间摔倒,被路遇的中学生们救回家里。外地出差的我,得到这个消息,心几乎都碎成了八片。但在心里还是默默祈祷,愿父亲仅仅是摔了一跤吧,千万不要发生其他什么不测。知道父亲的其他亲人都没时间来照应,我又在远路上,只好先委托我的一位当地挚友海龙,请他到我家,将我父亲赶紧送往县医院检查。他从我家七楼将我父背下,背到他的车里,然后去县医院拍了片。
一个可怕的消息发到了我的手机上---父亲的股骨头骨折了。
我说,先对我父亲保密吧。
坐在往回赶的车上,我心尤如雪上加了霜。我一边赶路,一边又约了一位何明朋友,他正好路过我家所在的县城。
见到父亲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八、九点了。他躺在医院走廊的一张平板推车上,一见我,他竟神情自若地安慰我:没事,就是擦破了一些皮,缓上几天就好了。
我真想埋怨他几句,还是忍了下来:咱有啥过不去的河?
父亲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我,再没吭声。
此前,就因为合作发生的那一幕,我曾多次劝诫过父亲,不要做您这个年龄不能再做的事了,不要去那些道路有问题的地方,以免发生意外,可他没听。
后面,更让我心情难平的是,父亲的摔跤,竟然是他背了超重的旧纸板,在去收废场的路上不幸摔倒的。一个八十四岁的老年人,自己走路都很容易摔跤了,居然还敢背着超重的东西,听了真相,我既心疼父亲的勤劳和无私又无奈于父亲的固执和无畏。
我去门诊办理相关缴费手续时,大夫的话更让我心痛。他说:这么大的年龄了没必要一定要去接骨,回去养着去,那是股骨头骨折,是骨头的死穴,即便使把骨头接上了也长不好。昨天就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,也是股骨头骨折,硬让我劝回去了。
我一听,对大夫起了火气:作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大夫,你这是在说什么?既就是我父亲的骨头接上了,后来没长好,做儿子的我才能问心无愧!
县医院的大夫却心平气和地一笑:我是劝你别花冤枉钱,这个手术做下来,多则得小十万元,少则也得五、六万,我是为患者经济条件考虑才劝你的。
我能说什么,只能说声对不起,便悄悄离开。
见了父亲,我直接说,大大,我们去甘肃中医院!
父亲:去干啥?
这个时候了,我不能不告诉他说,你是股骨头骨折了,得接上它。
父亲一听,忽然嚎啕大哭了起来:娃,我想你买房子花了那么多钱,又出版书,想帮你能挣一点算一点,哪怕是买一斤菜的钱,也是对你生活的填补。没想到,没想到这下把事干砸了啊,吽……
看到父亲如此的伤感和悔恨的样子,我再也忍不住悲怆的眼泪,抱紧父亲的推车也哭了起来。
父亲还是很坚强的:这么大个年龄了,接它干啥,我不去。
我说,大大,不管怎么,一定要给您接上。
父亲:我今天活不知道明天死的,别花那个钱,给我买个拐子就行了。
我说,不行,我要不惜一切,接好您的股骨头。
此时,朋友何明的车已来到了县医院门口。
父亲拗不过我,被我和何明抱上了车。
经过四十多天的治疗,虽然在医院熬坏了我,但父亲的股骨头接好了,那个年轻的李大夫说,只要营养跟上,就能长好。听到这话,我真想给他磕头。
没想到,一个八十四的老人,股骨头竟奇迹般地长好了。
父亲常常说:多亏我的儿子儿媳妇好啊,不然,我活不了这么大岁数。
而这时,母亲的身体时好时坏,我让她身边的儿女赶紧把母亲送过来。
父亲说,只要腿好了,身体就好了,他还可以照顾我的母亲。
这年春节,我们正在家里为父亲准备年饭,九哥忽然说他和夫人来给我拜年,已到我小区楼下。
九哥在合作也算是一个鼎鼎人物,我一个小蝌蚪,他怎么会给我来拜年。再说了,他曾说过,他不愿和不孝敬父母的人打交道,我也没给他解释什么,因为,我孝敬的是我自己的老人,只要老人晚年幸福,也没必要到外界去炫耀什么。好几年过去了,他突然又来造访,干什么?
来不及给睡午觉的父亲打招呼,我就赶忙下楼去接九哥。九哥和夫人来到我家。一寒暄,才知道九哥的来意。他是为当年他的道听途说来道歉的。我笑了笑,又摇了摇头。
九哥说:把你父亲请出来,我们说说话。他和父亲聊了很多很久,也说了他的来意。
临别,九哥握着我的手:我冤枉了你,对不起,但你却能包容我的过错,十分感激你。从老人的笑脸上,就能看出他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。其实,你对老人孝敬的有些细微之处,我自己都没做好啊。
九哥走后,父亲说:和你的这位朋友一聊,才知道他是一位领导,从他身上,我能看到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美德。
父亲啊,仅仅一个农民,但他总能理解出自己的家国情怀。
四年后的冬天,我在兰州参加鲁迅文学院甘肃班的培训,远处传来消息,说母亲过世了,父亲没能在最后的日子见到母亲边。
我赶忙休课,怀着一份说不清的怨,回家准备母亲的后事。
之后,父亲对我说:你妈妈这一走,我心里感觉一下子空落落的。
我说,您保重好身体,我妈妈在那边也能安心的。
父亲很悲恸:可能,我也该要走了。我连忙阻止父亲:您没病没灾的,饭也吃得好,别胡乱想,您的寿路还长着哩!父亲抬头看了一圈房顶:这一天,谁都躲不过啊!
2020年10月,是母亲去世的第十个月,国庆节假期满后,我便向单位续请了一段假。想多陪陪父亲的时光。
父亲说,人这一辈子,多好的时光都会过去,多好的时光都不会重来,一定要珍惜好时光。
不久,父亲就这么静静地走了,永远地走了。
记得四年前,看到我陪父亲来医院一定接上股骨头的决心,甘肃中医院父亲的主治医师李大夫请来众多专家,经过会诊得出一个方案,说老人的股骨头可以接好。后来的实践证明,他们的那次治疗非常成功,才使得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股骨头奇迹般地长好了,不用拐子还能上下楼了。
父亲与世长辞后,我朋友帮忙,请来骨科大夫,在不伤及股骨头整体连接的情况下,将已长进骨肉的钢架取了出来,以肉身如愿地将父亲葬进了他一生热爱的黄土地。
尽管,父亲的离去应了寿终正寝四个字,可在我的意识里,父亲的时光应该还很长,我还有好多话要和他说,可他再也听不到了……
作者: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,鲁迅文学院甘肃班学员,发表中短篇小说《红军曼巴》、《想寻找另一片天空》、诗歌、散文、评论等一百多篇。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《红撒拉》,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栅栏那边的羊群》等。

 English
English